欢迎来到勾陈一!
利维坦按:作为一个纳粹党党员,一个商人,奥斯卡・辛德勒曾挽救了众多犹太人的生命,但这也并不妨碍他挥霍无度、花天酒地的生活。没有那种“非此即彼”的道德观――当然,在此观念中,也要注意“不道德”和“非道德”的区分。在本文作者看来,有效的利他行为和独享一瓶红酒并不矛盾,他反对的是那种苦行式的道德绑架,其潜在逻辑在于,既然我如此要求自己,那么我身边的人也要按照这种标准行事。

图源:Angus R Shamal/Gallery Stock
“我很高兴,”备受赞誉的美国哲学家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如是写道,“不论我本人,还是我最亲近的人,都不是‘道德圣人’。”这一宣言见于沃尔夫某篇代表性随笔的开篇,随笔中,她构想了在道德层面达到完美会是什么样。假如你顺着沃尔夫的思想实验走下去,得出和她一样的结论,就会发现这个实验能将人救出道德完美的陷阱。
沃尔夫的文章《道德圣人》(Moral Saints,1982)设想了两种不同模式的道德圣人,她将它们分别命名为仁爱圣人(Loving Saint)与理性圣人(Rational Saint)。据沃尔夫描述,仁爱圣人总是快快乐乐地做出最符合道德的事:这样的人生并非没有乐趣,但道德考量是其绝无错误也不可动摇的核心。我们可以认为仁爱圣人是那种快活地卖光自己家当、把收入捐给饥荒救济会的人。理性圣人同样为道义奉献一切,但并非出于一种博爱的心态,而是源自责任感。
身边有个仁爱圣人可能比理性圣人更有趣些,但也有可能更让人抓狂,这取决于你的脾气如何。仁爱圣人时刻都很快乐,这会让她更好相处,还是会把你逼到崩溃边缘?事实上,美国学者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从佛教教义引申出了一条建议,教导人们“快乐地参与到人世间的苦痛中去”,而仁爱圣人在这点上做到了极致:但你也许会发现,在面对世上最可怕的经历时,仍然保持这样的快乐是愚蠢或不恰当的。另一方面,理性圣人孜孜不倦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可能也会让同伴觉得难以忍受。

电影《关于施密特》(About Schmidt,2002)剧照。图源:豆瓣电影
如果你自己并非圣贤,这两种道德圣人都很有可能给你带来困扰。他们会不会持续不断地打扰你,要求你付出更多?他们或许加入了有效利他主义运动(effective altruism),翻来覆去地建议你用最有效的方式来支配时间和可支配收入,以此帮助他人。
假如有人把大部分闲暇时间用来打电玩而非关注乐施会(译者注:Oxfam,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1942年成立于英国牛津),假如有人将大把闲钱花在红酒、巧克力这种奢侈品上,而非捐助给他人解决基本温饱,这样的人会给你带来什么感受?如果一个人把百分之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道德上,就很容易让你感到愧疚,你愿意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吗?
沃尔夫提出,如果一个人极度渴望成为道德圣人,也许会让自己变成周围人生活中的噩梦。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在他的小说《如何行善》(How to be Good,2001)中夸张地描绘了这一场景。但真正的圣人自然无比善良得体,或许不愿你一直感到不自在:这么做有什么好的呢?实际上,真正的圣人难道不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人吗?他们对于自己给你生活造成的影响理应十分清楚,就像他们明白自己给整个世界造成了多大影响一样。
沃尔夫认为,如果真是如此,新的问题就来了:道德圣人将不得不隐瞒对于你的道德层次的真实看法。不仅如此,按沃尔夫所言,若你讲了个违背道德的、愤世嫉俗的笑话,他们能真心地笑出声吗?说到底,他们有空和你一起出门闲逛吗?如果他们道德上完美无瑕,那必然有比逛街重要得多的事要做。
对于全心全意追求最高道德成就的人而言,有太多事物难以融入人生,朋友只是其中之一。假使道德圣人是完美的,他/她能把时间“浪费”在看电影、电视上吗?会花钱享受美食或旅游吗?会把精力用在运动、观鸟或远足上,而非去做更严肃要紧的事吗?他们肯定没时间去剧院看戏,也没心思蜷在被窝、沙发里享受读一本好书的乐趣。
据说王尔德(Oscar Wilde)在论及社会主义时曾说,极端利他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占用了太多美好的夜晚。如果恰好和手头的道德项目有关,道德圣人也许能找到时间做这些事:比如说,在慈善募款活动上看体育比赛,或是在前往急需援助的热点争议地区的途中欣赏风景。但倘若生命中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行善事,那么这些经历只能视作幸运的额外好处。
假如你没时间交友、娱乐、欣赏艺术或是观赏野生动物,那你就错过了沃尔夫所说的生命中非道德的那部分。沃尔夫并非在暗示非道德等同于不道德:仅仅因为某件事物与道德完全无关(例如打网球)并不意味着它就因此是道德败坏的。重点在于,从直觉上来看,道德关注的是诸如平等对待他人和试图减轻折磨这类议题。这些当然是好事:但和友人外出度假、去阿拉斯加雨林探险,或享受咖喱的美味也都是好事。道德上的善只是人生中美好事物的一部分,如果你将道德视为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物,那你的人生很可能在非道德层面上是极度贫瘠的。这意味着你错过了太多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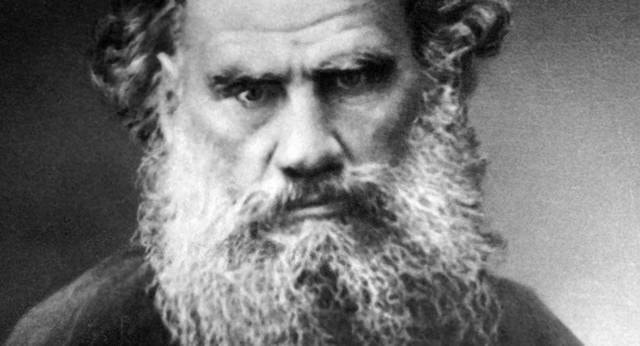
1846年,18岁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一次自嗨过后,终于尝试了一次易。他找了一个年龄偏大价格便宜的女人结束了自己的童贞,之后他在一篇日记里大骂自己,并诅咒女人:“谁是我们身上***放纵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吗?”图源:Famous Biographies
沃尔夫设想仁爱圣人的生活中不存在任何非道德的美好事物,并且他们对此全然满足。这种彻底禁欲的道德生活――没有友人、没有爱好,没有任何让人从道德事业分心的干扰――对仁爱圣人而言,并不以幸福为代价。但沃尔夫很好奇这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仁爱圣人看不到他所错过的一切么?假如他能意识到,这怎么能不影响他的幸福呢?
沃尔夫提出,或许仁爱圣人缺失了一部分感知力:一种看清生命中不只有道德的能力。这可能解释了仁爱圣人能一直保持快乐的原因。与之相对的是,沃尔夫不觉得理性圣人对自己错过了人生中一块巨大区域一无所知。沃尔夫猜测理性圣人仅凭一股责任感撑过了贫瘠的一生。可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把全部生命都献给道德事业,不顾其他一切呢?沃尔夫给出的答案让理性圣人也显得不那么理性了:也许他们的行为源自自我厌恶和(或)对罪罚的病理性恐惧。
沃尔夫的两种道德圣人版本建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最深远的两个道德哲学流派之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催生了沃尔夫的仁爱圣人)和康德哲学(Kantianism,催生了理性圣人)。沃尔夫问,如果你在生活中将这些道德观推到极致,你的人生会变成怎样?沃尔夫认为,如果彻底按这两种世界观生活,不论哪种都让人难以心向往之:如我们所见,这两种世界观各自构建了一种美好生活的愿景,它们意味着全身心地为他人的需要付出,没有一点时间供个人去享受生命中许多非道德的美好事物――事实上,它们意味着个人根本没有时间过自己的生活。引用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话来说就是,你将把自己的全部存在用来充当道德体系的仆役。

启蒙时代著名德意志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图源:Media Ethics in the Morning
如果“美好生活”这个说法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那么现代道德一定出了问题。
功利主义和康德哲学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两者都不很重视、甚至根本不重视个人幸福。功利主义哲学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如果多数人的需要要求你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包括牺牲个人的幸福,那你就必须这么做。沃尔夫的假想是正确的,一个完美的功利主义者,一个仁爱圣人,确实会是个幸福的人:这也确实是最理想的状态。
暂无评论

本站部分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仅供交流学习之用,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本站将尽快处理
Copyright(C)2023-2025勾陈一 ALLRights Reserved 勾陈一中文网 版权所有